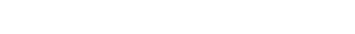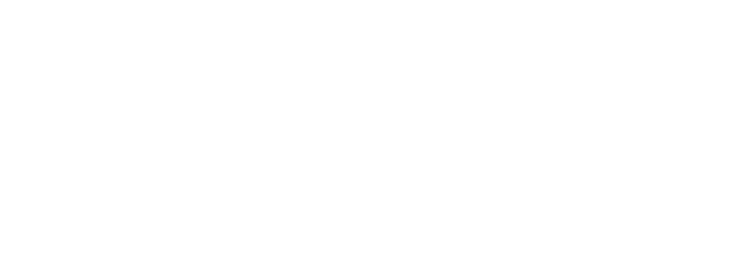【当事人及地位】
原告:(委托人)A进出口有限公司
被告:C货运代理公司
【基本案情】
A进出口有限公司(下称A公司)与德国B公司签订了一宗轮胎买卖合同,价格条款是FOB,价款大约15万美元。B公司指令青岛C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下称C公司)承运该票货物,后来A公司根据C公司的安排交付货物装船出运。因双方约定是电放,因此,C公司未签发正本提单。其中,提单副本显示,发货人是A公司,收货人是B公司,通知人是B公司。货物到达目的港后,C公司在没有得到A公司放货指令的情况下直接将货物交付给B公司。B公司收到货物后,以质量问题为由拒绝支付货款。A公司便委托我们在海事法院起诉了C公司,要求赔偿因擅自交付货物给其造成的全部经济损失。
【争议焦点】
本案涉及的焦点问题是,在电放方式下,承运人应当如何交付目的港货物?对此,实践中对指示提单和记名提单观点不一。
【代理过程及结果】
海事法院审理认为,C公司尽管辩称在没有正本提单的情况下交货给记名收货人并无不当,但其认可电放即意味着负有凭托运人指令才能放货的义务。C公司不能举证证明A公司指令其放货,那么其放货行为导致A公司失去收回货款的保障,应对A公司的全部经济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C公司不服一审判决上诉到省高院,要求改判驳回泰达公司的诉讼请求。二审中,双方观点针锋相对,争议激烈,合议庭三位法官也是意见不一,甚至一度考虑将该案提交给最高院来征求答复意见,以便在解决个案的同时,也为同类案件的审理寻求指导意见。本着互谅互让的和谐精神,在法院的多次居间调解下,双方最终达成和解。
【案例评析】
在电放方式下,承运人应当如何交付目的港货物?如果收货人一栏记载的是“TO ORDER”(即凭指示)字样,即便没有正本提单,承运人也应当根据托运人的指示交付给托运人指定的收货人,这在海事司法实践中基本达成共识,争议不大。如果提单副本或者提单复印件上收货人一栏记载明确,即是记名收货人,则承运人是否应当根据托运人指示交付货物则争议很大,观点也是截然相反。我们更倾向于“承运人须凭托运人指示才能交付目的港货物给收货人,否则承运人应当对托运人的货款损失承担赔偿责任”的观点。
持“承运人不必凭借托运人指示就可以交付目的港货物”的观点认为,由于承运人未签发正本提单,无法按照提单交付货物,也不能适用我国《海商法》有关凭提单货物交付的法律规定。在此情况下,货物如何交付应当适用我国《合同法》之规定。按照《合同法》第309条的规定,货物运输到达后,承运人知道收货人的,应当及时通知收货人,收货人应当及时提货。收货人逾期提货的,应当向承运人支付保管费用。按照上述法律规定,货到目的港后,承运人即可交付货物给收货人。江平教授主编《合同法精解》对309条的注释中称,在无提单签发时,运送货物到达目的地后,经收货人提出交付请求,收货人即取得托运人因运送合同所取得的权利,故收货人的交付请求权即提货权,源于运输合同。
此外,持此观点的人还认为,电放交付货物应当参照海运单的做法。众所周知,海运单项下,承运人在货到目的港后即可根据收货人请求交付货物。为了证明上述观点的正确性,下述例子经常被引用:托运人委托快递公司给指定收货人快递物品,货物到达目的地后,快递公司作为承运人根本不需要托运人的指示就可以将货物直接交付给收货人,交付货物后快递公司作为承运人就完成了运输义务,根本无须托运人的指示。在海事司法实践中,有支持上述观点的典型判例。青岛海事法院作出的案号为(2004)青海法威海商初字第92号判决书写明,原告即托运人将货物交由被告即承运人承运后,货物所有权转移给收货人。在原告既不持有正本提单,又不能提交非凭其指示不得放货的证据的情况下,被告将货物交付给记名收货人,不构成对原告的违约。因此,原告要求被告承担货款损失的诉讼请求,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持“承运人须凭托运人指示才能交付目的港货物给收货人”的观点认为,理论界和实践界将电放交货的形式归纳为:由托运人向承运人提出电放申请并提供保函后,由承运人(或其代理人)以电报、电传通知目的港代理,该票货物无须凭正本提单放货。因此,托运人何时要求承运人电放是托运人的权利。换言之,承运人只能根据托运人的电放申请才能在目的港直接交付货物给收货人。如果承运人没有托运人电放申请或者电放指示就直接交付货物岂不侵犯了托运人的货权?在司法实践中,有支持上述观点的典型判例。大连海事法院作出的案号为(2002)东商初字第24号判决书中写明:按照交易习惯,电放即是承运人在货物装船时并不向托运人签发提单,而是根据托运人电讯指令将货物放给收货人。被告即承运人在未得到原告指示的情况下将货物交付给收货人,致使涉案货物在原告即托运人未收回货款的情况下被收货人提领,被告应当对原告的货款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我们倾向于后一种观点。
首先,我国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电放操作中不具有可转让性的海运合同即为海运单,并由此合乎逻辑的要求承运人只承担向记名的收货人交付货物的责任。
其次,托运人在托运资料中指定了记名收货人,这不构成托运人向承运人发出的交货指令。托运人在托运资料中指定记名收货人仅仅是告知承运人应当将货物交付给谁。换言之,这仅仅是使该收货人成为我国《海商法》第42条所规定的“有权提取货物的人”。至于承运人何时应向该收货人交付货物则完全应当根据托运人的另外电放指示。从电放的流程和模式看,电放是一个承托双方互动的过程,首先托运人不要求承运人签发正本提单并指定记名收货人;其次托运人结合其国际贸易环节,特别是结算环节的进展决定何时应当向承运人发出电放指令;再次,承运人得到托运人电放指令后立即通知其目的港代理;最后,记名收货人向承运人的目的港代理提领到港货物。从上述过程看,托运人在托运资料中指定记名收货人,本身不构成交付货物的指令。
第三、从法律适用来讲,我们认为应当适用《海商法》、海商法原理或者学理及海事海商惯例。如前所述,电放能够证明托运人与承运人之间存在着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关系,具有海上货物运输合同之证明的功能。电放方式下的货物交付虽然不能按照提单相关法律规定来约束承运人,但直接适用我国《合同法》来调整双方海上货物运输项下的权利和义务关系似乎不妥。大家知道,海商法具有相当的独立性,有民法不能对应的特殊制度。正如海商法专家郭瑜教授 “用尽海商法原则”所提倡的,海商法调整范畴的问题,应当尽量适用海商法解决。海商立法,海事国际惯例,海商法原则、原理和学理都是解决问题的依据。处理类似的问题,民法一般性规定可以作为参照。只有海商法调整范围以外而又属于民法调整范围的问题,才能直接适用民法的一般性规定。因此,在海上货物运输合同中,电放下的货物交付问题不宜直接适用《合同法》和其他民法的相关规定。综上,从法律依据角度而言,承运人引用《合同法》第309条之规定主张交付目的港货物无需托运人电放指示就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第四,电放方式下的货物交付虽然不能依据提单相关法律规定,但应当考虑到海上货物运输的特点和海运实践中电放模式的特点来综合考量。在海上货物运输中,托运人和收货人一般是买卖双方,托运人在未收回货款的情况下,首先要控制货物及货权。如前所述,为了避免“货等单”产生高额目的港费用的情况下,电放成为承托双方的共同选择。然而,托运人选择电放并不意味着放弃了货物本身更不是放弃了货权,其仅仅是表明收货人不必持有正本提单在目的港提货而已。因此,是否电放货物,何时电放货物给收货人都是托运人的权利,相对应而言也是承运人的义务。因此,承运人应当根据托运人指示交付货物给记名收货人。
随着国际集装箱运输业的飞速发展,提单晚于货物到达目的港的现象增加,尤其是近洋运输,“货等单”的问题给买方及港口都造成了不便,甚至损失。提单的流程遇到了严峻的挑战,由此电放交付货物的方式应运而生。虽然电放提单具有高效、便捷的特点,但电放的实施是建立在买卖双方及承托双方等各方面彼此信赖的基础之上的,这种信赖非常脆弱,一旦发生贸易环节的纷争,必然会导致电放法律纠纷的层出不穷。据我们了解,各地海事法院受理的此类电放案件大幅上升。
由于电放的法律性质相当复杂,又没有国内现有法律渊源的明确规定,不同的海事法院甚至同一海事法院的不同法官会就同一类电放案件作出截然相反的裁判。因此,我们建议,对于托运人而言这种交付货物的方式存在很大风险,建议托运人在货物出运时与承运人作出“虽不签发正本提单,但货到目的港后必须等待托运人的指示才能交付货物”的书面特别约定,以保护托运人对货物的控制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