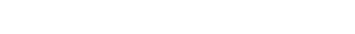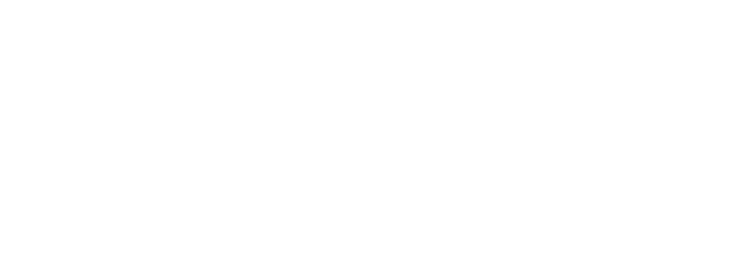监管趋势:禁止上市公司及其股东作出定增保底承诺
从司法机关的态度来看,2019年11月8日,最高院发布的《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以下简称“《九民纪要》”)第5条规定,投资方与目标公司订立的“对赌协议”在不存在法定无效事由的情况下,目标公司仅以存在股权回购或者金钱补偿约定为由,主张“对赌协议”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定增保底协议作为一种特殊对赌,其效力也在《九民纪要》的前述规定下得到了承认。
从监管机关的态度来看,2020年2月14日,中国证监会发布的《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简称“《实施细则》”)第29条首次在监管层面对定增保底承诺作出否定评价。根据《实施细则》第29条,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主要股东不得向发行对象作出保底保收益或变相保底保收益承诺,且不得直接或通过利益相关方向发行对象提供财务资助或者补偿。目前,《实施细则》已被2023年2月17日出台的《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所替代,新规第66条[1]保留了《实施细则》第29条的规定,同日修订发布的《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第38条[2]也新增了类似规定。可见,中国证监会作为监管机关,其对定增保底承诺持否定态度。
随着近年来对金融板块监管力度的加强,司法部门对定增保底协议效力的态度也开始发生改变。2022年6月23日,最高院出台发布《关于为深化新三板改革、设立北京证券交易所提供司法保障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新三板意见》”),其中第9条明确规定:“在上市公司定向增发等再融资过程中,对于投资方利用优势地位与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者主要股东订立的‘定增保底’性质条款,因其赋予了投资方优越于其他同种类股东的保证收益特殊权利,变相推高了中小企业融资成本,违反了证券法公平原则和相关监管规定,人民法院应依法认定该条款无效”。由此可见,司法部门对定增保底协议效力也开始持倾向性的否定态度。

(一)《实施细则》颁行前的司法裁判情况
鉴于定增保底协议被视为一种特殊的对赌安排,在《实施细则》颁行前,法院在认定其效力的过程中多参考最高院在“对赌第一案”(2012)民提字第11号公报案例海富案中确立的“与公司对赌无效,与股东对赌有效”的裁判规则。除此之外,在(2017)最高法民终492号贵阳工投系列案件中,最高院认为定增保底承诺约定本质上系目标公司股东与投资者之间对投资风险及收益的判断与分配,属于当事人意思自治范畴,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因此认定保底承诺有效。
(二)《实施细则》颁行后,《新三板意见》颁行前的司法裁判情况
虽然中国证监会在其监管规范中对上市公司及其股东作出的定增保底承诺进行了否定,但法院在司法裁判中仍基本认定该约定有效。从笔者检索到的案例来看,法院的裁判理由如下:
1.法不溯及既往。由于《实施细则》从2020年2月14日颁布实施,其颁行后法院处理的大量纠纷中所涉定增保底协议系《实施细则》发行前签订的。根据法不溯及既往的原则,其只能适用于实施后发生的法律事实,对此前发生的行为并无溯及力。因此,部分法院以定增补足承诺发生在《实施细则》颁行前,不适用现有规定为由,认定该约定有效,如(2021)最高法民终423号、(2020)最高法民终1161号、(2018)皖17民初251号案件。
2.《实施细则》不属于导致合同无效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根据《民法典》第153条第1款的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鉴于《实施细则》为中国证监会发布的部门规章,部分法院以部门规章不能直接导致合同无效为由,在该约定违反《实施细则》规定的情况下,仍认定约定有效,如(2021)最高法民申4805号、(2020)最高法民终1294号、(2020)最高法民终1295号、(2018)皖17民初251号案件。
3.定增保底承诺的风险可控,不损害特定法益。部分法院认为,一方面,定增保底承诺系上市公司股东对特定少数主体做出的,针对的并非证券市场中的不特定投资者,其应当被视为当事人针对投资风险及收益分配的内部约定,属于当事人意思自治范畴,如(2021)京民终97号、(2021)京民终292号、(2020)京民终251号、(2020)沪民终337号、(2020)浙07民终2152号案件;另一方面,定增保底承诺所针对的客体为上市公司定向增发的股票,而非已经在二级市场上自由流通的股票,一般不会造成股价的大幅波动从而危害金融秩序,如(2021)最高法民申2922号案件。基于此,法院通常认为定增保底承诺并不会损害公司及其股东、债权人利益,也不损害证券市场秩序或社会公共利益,故而认定有效。
(三)《新三板意见》颁行后的司法裁判情况

从上述梳理情况来看,法院似乎并未因相关监管规范和司法文件的出台而改变裁判思路,但这是否意味着今后上市公司及其股东作出定增保底承诺时就能高枕无忧?笔者认为并不尽然,在当今金融强监管的趋势下,结合最高院对金融规章效力的关注,当今形势下定增保底的效力问题仍存在讨论空间。
(一)金融规章位阶限制的突破路径
根据《民法典》第153条第1款之规定,规章不属于判断合同效力的直接依据。因此,虽然《实施细则》《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等金融规章均对定增保底承诺做出了禁止性规定,仍有很多法院以规章的位阶不足以限制合同效力为由认定其有效。然而,金融规章的禁止性规定虽然不能直接导致合同无效,但可以通过其他路径对合同效力产生影响。
在2023年1月10日召开的全国法院金融审判工作会议(以下简称“会议”)上,最高人民法院审委会委员刘贵祥法官发表讲话,明确了“金融规章虽然不能作为认定金融合同无效的直接依据,但可以作为判断是否违背公序良俗的重要依据或裁判理由……规章中关于维护金融市场基本秩序、维护金融安全、防控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禁止性规定,可以用来识别是否违反公序良俗。在金融监管规章有关条款构成公序良俗的情况下,可以适用《民法典》第153条第2款的规定认定合同效力”。[3]
除此之外,会议还指出:“一些金融监管规章的强制性规定是根据上位法的授权或者是为了落实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而制定的具体规定,有上位法的明确依据,只不过该上位法的规定较为原则,其在结合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将该原则性的规定予以具体化,使其具有可操作性。在这种情况下,合同违反的是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人民法院可依据《民法典》第153条第1款认定合同效力”。[4]
由此可见,若金融规章的禁止性规定可以通过两条路径导致合同无效:一是该规定本身是上位法原则性规定的具体化,二是其规定所保护的法益构成公序良俗。
而定增保底协议是在上市公司定向增发等再融资过程中,投资方利用优势地位与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者主要股东订立的。这一约定赋予了投资方优越于其他同种类股东的保证收益特殊权利,变相推高了中小企业融资成本,即使其所针对的是特定少数投资者,仍对上市公司的其他投资者产生不公。
因此,一方面,定增保底协议所涉金融规章的禁止性规定本身即为《证券法》第3条[5]所规定“公平原则”的具体化,人民法院可以依据《证券法》第3条这一强制性规定认定该约定无效。另一方面,“公序良俗”可以被理解为公共秩序和善良风俗,而投资者利益保护则是证券市场公共秩序中的重要内容。相应金融规章所保护的重要法益之一即为被定增保底承诺排除在外的其他投资者的利益。因此,金融规章对定增保底协议的相关规定构成公序良俗,人民法院可以定增保底协议违反公序良俗为由,依据《民法典》第153条第2款判决该约定无效。
对此,在苏州市中院发布的《2019-2021年度苏州法院公司类案件审判白皮书暨典型案例》的案例六某机电公司诉某投资公司确认合同无效纠纷案中,法院即以相关投资保底协议违反证券法规定和公序良俗为由确认协议无效[6];在华鑫国际信托有限公司诉深圳市名家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合同纠纷案中,西城区法院也认为差额补足协议损害投资者的合法权益、资本市场交易秩序及金融安全,最终以其违反《证券法》和《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为由认定该约定无效[7]。虽然前述两则案例均无法通过公开检索到裁判文书原文,其裁判要旨仅能从新闻报道中窥见一二,但仍应该看到,金融规章突破位阶限制影响合同效力的以上两条路径具备一定可行性。
(二)《新三板意见》适用范围的扩张
《新三板意见》对于定增保底协议效力的否定似乎本可以视为最高院在金融强监管的趋势下,对定增保底裁判走向的转变。但其颁布后仍有部分法院认为其适用范围仅限于新三板挂牌的上市公司,导致实践中《新三板意见》的影响范围有限。对此,笔者认为《新三板意见》的该项约定能否扩张适用到其他板块上市公司,取决于新三板上市公司与沪深交易所上市公司的区别是否会影响这一规定所保护的法益。
从《新三板意见》第9条的规定来看,其认定定增保底协议无效的重要原因在于这一约定赋予了投资方优越于其他同种类股东的保证收益特殊权利,推高中小企业融资成本的同时,损害了其他同种类股东的合法权益。因此,这一规定所保护的法益除了融资企业利益外,还包括投资者的合法权益。而相比于新三板上市公司,沪深交易所上市公司虽然规模更大、发展阶段更加成熟且与投资者的地位更加平等,在此基础上不同板块、不同交易所对其融资企业的法益保护力度存在差异,但对投资者的权益保护却并无不同。
因此,即使沪深交易所上市公司并不会因为作出定增保底承诺而增加融资成本,但被该承诺排除在外的其他投资者的利益却将同样因此受到损害。因此《新三板意见》该项规定的裁判意旨应当扩张适用到其他板块及交易所的上市公司,不应局限于新三板。

鉴于新规颁行时间较短,最高院对金融规章的重视也仅初见苗头,且在新规颁行前既存的定增保底协议数量繁多,若均认定无效,必然会对证券市场秩序产生影响。因此在短期内,定增保底承诺的效力或仍被司法裁判所认可,从笔者近期检索到的司法案例情况来看也可见一斑。
【注释】
1.《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2023修订)》第38条规定:“上市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证券的,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主要股东不得向发行对象做出保底保收益或者变相保底保收益承诺,也不得直接或者通过利益相关方向发行对象提供财务资助或者其他补偿。”
2.《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第66条规定:“向特定对象发行证券,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主要股东不得向发行对象做出保底保收益或者变相保底保收益承诺,也不得直接或者通过利益相关方向发行对象提供财务资助或者其他补偿。”
3. 刘贵祥:《关于金融民商事审判工作中的理念、机制和法律适用问题》,《法律适用》2023年第1期,第15页。
4. 刘贵祥:《关于金融民商事审判工作中的理念、机制和法律适用问题》,《法律适用》2023年第1期,第16页。
5.《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第3条规定:“证券的发行、交易活动,必须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
6.《护航企业发展,优化营商环境:苏州中院发布公司类纠纷案件审判白皮书和典型案例》https://mp.weixin.qq.com/s/fAQsMhcBtLZEypGCT_hSkA
7.《名家汇实控人为定增“兜底”,“抽屉协议”一审被判无效,华鑫信托提起上诉》https://mp.weixin.qq.com/s/Y1NUTAHH6nuIm2UTYwC13g


张慧

文康商事诉讼与破产清算团队
文康商事诉讼与破产清算团队自2007年设立以来,先后担任百余家破产、重整与强制清算企业的管理人、清算组、投资人顾问及债权人、债务人顾问,组织和主持了大量的企业破产与清算工作,擅长从各个角度权衡判断商业风险并及时提供代表各自利益最大化的建议和解决方案,专业能力得到各级司法部门和当事人的高度评价。

本文作者
专栏文章
-
公司治理
股东间协议在有限责任公司治理中的效力认定
笔者结合相关案例对此问题进行分析2023-11-21 -
公司治理
合作协议中那些隐秘的角落
本文以普法和警示为目的,从最基础的、“不起眼”的、容易被忽视的条款说起,希望对非专业投资人士有所裨益。2023-11-06 -
公司治理
金融强监管背景下定增保底协议的效力问题分析
笔者结合相关监管规范和司法案例进行综合分析。2023-10-30 -
公司治理
一致行动人协议的效力认定和解除权的行使
本文尝试结合现行法律法规和司法实践对一致行动人协议的效力和解除权行使问题进行探讨,并提出具体的解决路径,以供参考。2023-09-05 -
公司治理
实际出资人在股权代持中常见的法律风险及防范措施
本文通过案例分析实际出资人会面临的法律风险并提出防范建议。2023-02-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