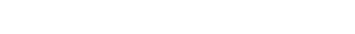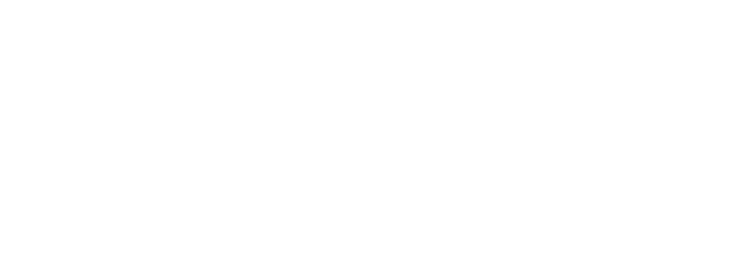在司法实践中,将注册商标用于商品、包装、容器类等所引发的商标犯罪比较典型、常见。但在以互联网为依托的新业态经济环境下,将注册商标用于交易文书、广告宣传等非典型案件中,如何认定“商标使用”确存在较大争议。本文以最高人民法院案例库入选的首批知识产权案件之一为研究对象,对新业态商标犯罪中如何认定刑法意义上的“商标使用”进行初步分析。

基本案情
被告人罗某洲、马某华分别系“昇某公司”和“聆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2020年9月,两人经密谋后以各占50%股份的使用方式,借助两公司场所、人员及生产设施,合作组装假冒某果注册商标的蓝牙耳机并对外销售牟利。组装生产的蓝牙耳机成品没有商标标识,但与某果手机配对时会出现“Airpods”或“Airpods Pro”的电子弹窗。
侦查机关在昇某公司住所地抓获罗某洲、李某、王某汝、向某等人,并查获疑似假冒二代某果蓝牙耳机1900个,疑似假冒三代某果蓝牙耳机6700个(均无商标标识,但连接某果手机后会显示“Airpods”或“Airpods Pro”标识的弹窗)等物品。在聆某公司生产场地抓获马某华、梁某意、吕某芳、明某等人,并查获1546个包装完整的疑似假冒某果三代蓝牙耳机(有某果商标,连接后弹窗显“Airpods Pro”)、319个未包装的疑似假冒某果三代蓝牙耳机(外包装有某果商标,连接后弹窗显示“Airpods Pro”)、5600个未包装的疑似假冒某果三代蓝牙耳机(无某果商标,连接后弹窗显示“Airpods Pro”)、100个某果牌蓝牙耳机包装盒、2163个未包装的疑似假冒某果二代蓝牙耳机(包装有某果商标,连接某果手机后弹窗显示“Airpods”)、100个完整包装的疑似假冒某果二代蓝牙耳机(充电仓上有DESIGNED BY APPLE IN CALIFORNIA商标,包装盒上有标识,耳机连接后弹窗显示“Airpods”)及测试机、测试仪、电烙铁、原材料,电脑主机、单据、销售价格清单等物品。案涉假冒某果蓝牙耳机及包装无论是否印有某果注册商标,经蓝牙连接某果手机后均弹窗显示“Airpods”或“Airpods Pro”标识。

裁判要旨
1.《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4〕19号)第八条第二款规定,刑法第二百一十三条规定的“使用”,是指将注册商标或者假冒的注册商标用于商品、商品包装或者容器以及产品说明书、商品交易文书,或者将注册商标或者假冒的注册商标用于广告宣传、展览以及其他商业活动等行为。商标识别商品来源的功能是商标的基本和首要功能,生产经营者使用商标标明商品的来源,消费者通过商标来区别同类商品,了解商品,做出选择。假冒注册商标犯罪中“使用”不限于将商标用于商品、商品包装或者容器等有形载体中,只要是在商业活动中用于识别商品来源的行为均构成商标性使用。判断是否构成假冒注册商标罪,应当综合被告人的主观意图、使用方式和相关公众的认知来判断是否在商业活动中造成消费者的混淆和误认。

律师评析
1.刑事司法领域
2005年《人民司法》第一期刊载的《<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理解与适用》一文中指出,关于刑法第二百一十三条中的“使用”,该《解释》参照《商标法实施条例》(2002年)第三条的规定进行了明确。事实上,《商标法》在一开始并未明确规定“使用”一词的概念。2002年《商标法实施条例》第三条明确了该规定,商标法和本条例所称商标的使用,包括将商标用于商品、商品包装或者容器以及商品交易文书上,或者将商标用于广告宣传、展览以及其他商业活动中。因此,2004年两高出台的《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只能参考2002年的《商标法实施条例》。
《商标法》在2013年修订时,吸收了2002年《商标法实施条例》的规定,在第四十八条规定,“本法所称商标的使用,是指将商标用于商品、商品包装或者容器以及商品交易文书上,或者将商标用于广告宣传、展览以及其他商业活动中,用于识别商品来源的行为。”直到此时,司法实务界才真正将建立起以“识别商品来源”为落脚点的“商标使用”概念。2013年修订《商标法》的立法解释明确指出:“商标使用是以识别商品来源为目的的将商标用于商业活动的行为。如果不是以识别商品来源为目的的使用商标,或者将商标用于非商业活动中,都不构成本法意义上的商标使用。”2014年修订《商标法实施条例》时,未再明确规定商标使用的具体定义、概念。
在之后的两高等部门出台的《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均未再对“商标使用”进行规定。
2.行政执法领域
为加强商标执法指导工作,统一执法标准,提升执法水平,强化商标专用权保护,国家知识产权局于2020年6月15日印发《商标侵权判断标准》。其中第三条规定,判断是否构成商标侵权,一般需要判断涉嫌侵权行为是否构成商标法意义上的商标的使用。商标的使用,是指将商标用于商品、商品包装、容器、服务场所以及交易文书上,或者将商标用于广告宣传、展览以及其他商业活动中,用以识别商品或者服务来源的行为。
第四条 商标用于商品、商品包装、容器以及商品交易文书上的具体表现形式包括但不限于:(一)采取直接贴附、刻印、烙印或者编织等方式将商标附着在商品、商品包装、容器、标签等上,或者使用在商品附加标牌、产品说明书、介绍手册、价目表等上;(二)商标使用在与商品销售有联系的交易文书上,包括商品销售合同、发票、票据、收据、商品进出口检验检疫证明、报关单据等。
第五条 商标用于服务场所以及服务交易文书上的具体表现形式包括但不限于:(一)商标直接使用于服务场所,包括介绍手册、工作人员服饰、招贴、菜单、价目表、名片、奖券、办公文具、信笺以及其他提供服务所使用的相关物品上;(二)商标使用于和服务有联系的文件资料上,如发票、票据、收据、汇款单据、服务协议、维修维护证明等。
第六条 商标用于广告宣传、展览以及其他商业活动中的具体表现形式包括但不限于:(一)商标使用在广播、电视、电影、互联网等媒体中,或者使用在公开发行的出版物上,或者使用在广告牌、邮寄广告或者其他广告载体上;(二)商标在展览会、博览会上使用,包括在展览会、博览会上提供的使用商标的印刷品、展台照片、参展证明及其他资料;(三)商标使用在网站、即时通讯工具、社交网络平台、应用程序等载体上;(四)商标使用在二维码等信息载体上;(五)商标使用在店铺招牌、店堂装饰装潢上。
第七条 判断是否为商标的使用应当综合考虑使用人的主观意图、使用方式、宣传方式、行业惯例、消费者认知等因素。
从上述条文可知,该些规定具体细化了《商标法》的规定,对行政执法如何认定“商标使用”提供了更为清晰、明了的适用依据。
3.民法司法领域
最高院的《关于审理商标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20〕19号)并未对商标使用进行规定,从司法实践看,更多依据《商标法》的相关规定。

结语
两高向社会公开的《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征求意见稿)也未再就“商标的使用”问题进行规定。如果最终出台的的司法解释不再明确规定“商标使用”的具体内涵,那么本文所引案例或将成为司法实践的重要参考案例。诚如裁判要旨所言:“判断是否构成假冒注册商标罪,应当综合被告人的主观意图、使用方式和相关公众的认知来判断是否在商业活动中造成消费者的混淆和误认。”
二审: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2022)粤03刑终514号刑事裁定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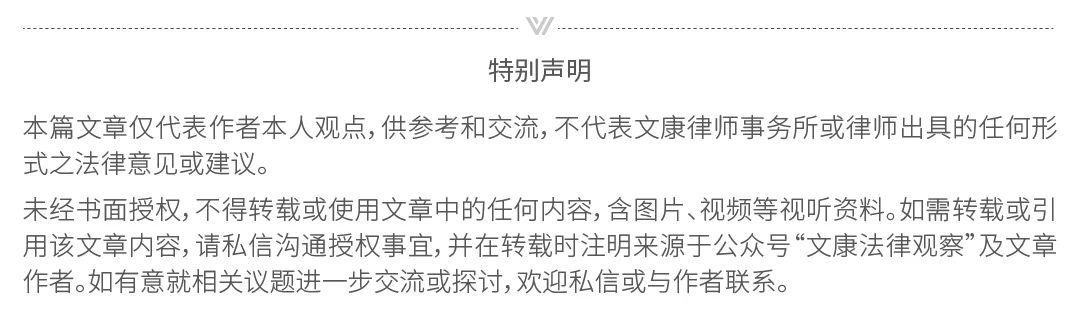
专栏文章
-
知识产权
企业出海中的常见知识产权风险及应对措施
本文结合最新行业数据与典型案例,拆解出海浪潮下的知识产权风险与破局之道。2025-11-27 -
知识产权
网络信息作为现有技术抗辩证据的认定
专业解读2025-07-21 -
知识产权
商标侵权惩罚性赔偿裁判逻辑探析
本文通过两起典型案件,结合相关司法解释,剖析商标侵权案件中惩罚性赔偿的裁判逻辑。2025-06-20 -
知识产权
保税仓库知识产权风险防范探析
全国知识产权宣传周2025-04-22 -
知识产权
知识产权诉讼中共同侵权的构成要件及责任承担
全国知识产权宣传周2025-04-21 -
知识产权
数据资产保护路径与登记功能——以北知院首例已登记数据资产不正当竞争纠纷案为例
本文在梳理本案判决的基础上,结合相关理论研究,探讨数据资产的保护路径以及数据知识产权的登记功能。2024-08-27 -
知识产权
驰名商标在民事侵权诉讼中的认定路径探析
专业解读2024-04-26 -
知识产权
字号保护的司法判断标准
本文通过梳理相关资料,详细阐释字号获得保护的法律构成要件和司法裁判标准。2024-04-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