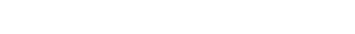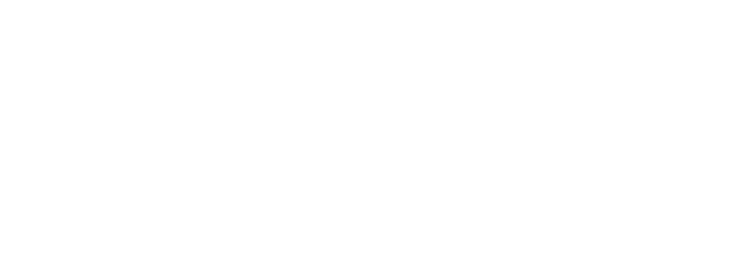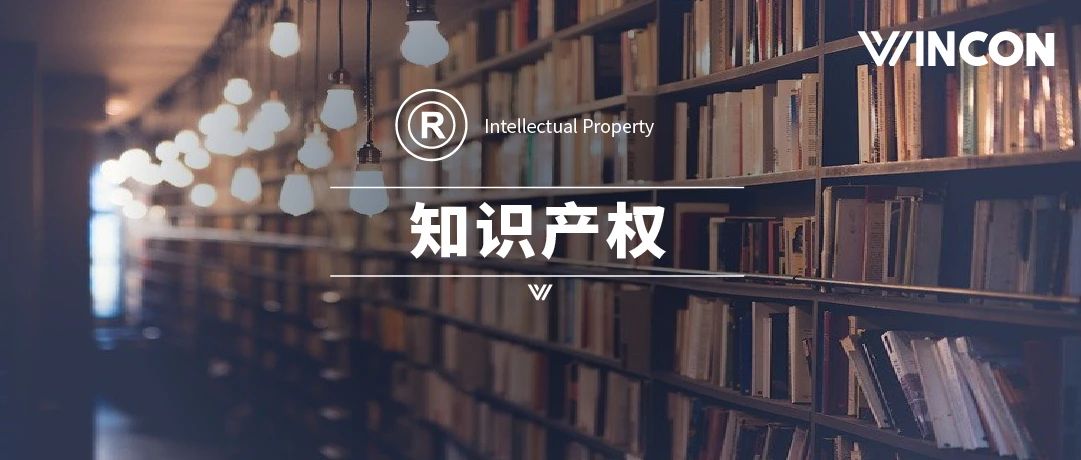
摘要:字号作为商业标识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成为彰显企业良好市场信誉和优质产品质量的载体,具有重要商业价值,是企业的重要无形资产。本文通过梳理关于字号保护的法律法规、研究典型司法裁判文书并结合理论观点,详细阐释字号获得保护的法律构成要件和司法裁判标准,以期帮助企业更合理地运营企业字号,增加企业资产。
字号作为商业标识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识别不同企业的重要功能,可以成为彰显企业良好市场信誉和优质产品质量的载体,因此具有重要商业价值,是企业的重要无形资产。
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市场活力的不断释放,我国企业数量自党的十八大以来呈爆发式增长。根据国务院发布的《2023中国经济年报》及中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统计的数据显示,截至2023年底,我国市场主体总数近1.81亿户,其中登记在册的民营企业超5300余万户。
因字号在相当程度上体现了企业家的商业情怀、经营理念和发展远景,所以投资者倾向于在企业设立之时为其选取寓意美好的词汇作为字号,这就促使良词佳句“需求旺盛”,导致企业字号相同或类似的现象屡见不鲜。
因此,加强企业字号的管理和保护,有利于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塑造公平合理的市场竞争秩序,保障市场经济的绿色健康发展。但字号相同或类似的企业,因行业领域不同、经营业务不同、行政区域不同,不必然产生需要司法介入调整的冲突,企业字号也需要满足一定的条件才能获得司法的保护。
由于我国没有专门的针对字号保护的法律法规,因此理论和实务中围绕字号的保护多有争论。本文试图通过梳理关于字号保护的法律法规、研究司法裁判文书并结合理论观点,来详细阐释字号获得保护的法律构成要件和司法裁判标准,并据此提出为企业字号提供保护的相应措施,以期帮助企业更合理地运营企业字号,增加企业资产。

(一)字号是企业名称的核心构成要素
根据2020修订版《企业名称登记管理规定》第六条规定,企业名称由行政区划名称、字号、行业或者经营特点、组织形式组成。其中,跨省、自治区、直辖市经营的企业,其名称可以不含行政区划名称,跨行业综合经营的企业,其名称可以不含行业或者经营特点。
可见字号是企业名称的必要组成部分,不可缺少。尽管组织形式也是企业名称的必要组成部分,但因组织形式的法定性及类型的相对固定性,决定了组织形式通常不会成为企业名称中具有识别功能的组成部分,而仅表示企业的法律性质。
由此,字号便成为企业名称的核心构成要素,是体现企业名称标识功能的重要载体。
(二)字号并非单独的权利客体,其通常作为企业名称受到保护
字号是企业名称的核心构成要素,意味着字号失去了作为单独权利类型进行司法保护的必要性,而不具区分功能的企业字号通常无法作为企业名称予以司法保护[1]。
《民法典》第一百一十条明确赋予了企业名称权,但是并未赋予企业字号权,仅把具有一定知名度的字号作为企业名称权的扩展保护内容,即只有在字号具有一定社会知名度,被他人使用足以造成公众混淆的情形下,可以参照适用名称权的规定保护相关字号,这说明我国现行法律并未将企业字号纳入权利客体的保护范围。
尽管有部分观点认为,应当将字号确定为企业的单独权利客体之一[2],但笔者认为,字号的功能与企业名称的功能基本相同,且字号是企业名称的核心构成要素,在现行立法和司法通过企业名称权扩展保护知名字号和反不正当竞争法及其司法解释可以保护公平竞争法益的情形下,没有单独设立字号权的立法必要性。
(三)概念的厘清与立法衍变:字号不同于商号,商号等同于企业名称
在较长一段时间内,我国理论和实务界对字号与商号的界定存在较大争议。
部分学者认为,字号即商号。如任先行、周林彬教授认为,商号和商业名称是种和属的关系,商业名称是种,而商号是属,商号是商业名称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核心部分。[3]实务层面,1991年制定的《企业名称登记管理规定》及2012年修订的《企业名称登记管理规定》均将字号等同于商号,“企业名称应当由以下部分依次组成:字号(或者商号,下同)、行业或者经营特点、组织形式。”浙江省2021年修正的《浙江省企业商号管理和保护规定》第三条亦明确,商号即字号。
反对观点认为,商号不同于字号,商号与企业名称是同一概念。如张民安教授认为,商事名称又称为商号,是指商人在经营活动中用来表彰自己的经营活动和区分他人经营活动的名称。[4]
字号、商号与企业名称的学术争议,其实主要源于对国际条约和国外有关“商号”立法的翻译和对法律概念的理解存在差异所导致。陈乃蔚教授和魏来教授认为,学术界有不少论述商号权利的文章,引用一些国际条约和外国有关商号的立法进行比较,将商号与字号混为一谈,殊不知此商号非彼商号,因语言及法律概念内涵外延的差异造成了某些不必要的学术争论。实际上,一些外国立法及有关国际条约中的商号概念和我国的商号概念有很大区别,大体上相当于我国的企业名称。[5]
我国立法的衍变也印证了字号不同于商号,而商号同于企业名称的观点。2020年修订的《企业名称登记管理规定》已经不再将字号等同于商号,2021年1月1日修改施行的《民事案由规定》154企业名称(商号)合同纠纷及163侵害企业名称(商号)权纠纷,也明确了商号等同于企业名称。

《民法典》第107条规定,具有一定社会知名度,被他人使用足以造成公众混淆的字号,参照名称权保护的相关规定。《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六条第(二)项规定,经营者擅自使用他人有一定影响的企业名称(包括简称、字号等),造成混淆,是不正当竞争行为。而《不正当竞争司法解释》第六条则进一步界定,具有一定的市场知名度、为相关公众所知悉的企业名称中的字号,可以认定为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定的“企业名称”。
可见,字号获得保护的法律构成要件为:
(一)具有一定的社会知名度,这是字号保护的前提
1.字号区别不同经营者的功能是其可以作为企业名称权延展保护内容的根本所在,而区别功能的司法判断标准在于具有一定的社会知名度。
如前所述,字号保护的必要性在于其具备了区别不同经营者的功能,区别功能的具备则是建立在经营者持续不断地使用和宣传推广,令相关公众将字号与特定经营者建立起较为稳定联系的基础之上。一旦公众与经营者之间建立的纽带形成,经营者所使用的字号便具有了较高的市场知名度。
因此,具有一定社会知名度的字号才可以作为企业名称权进行保护,而不具有一定社会知名度的字号难以获得此种保护。
2.字号有一定影响的司法判断标准同于具有一定的社会知名度或市场知名度的判断标准。
2017年修订的《反不正当竞争法》扩大了商业标识的保护范围,将“有一定影响”的字号明确纳入企业名称的保护范围,但是2020年修正的反不正当竞争法司法解释依然沿用2007年反不正当竞争司法解释关于字号保护的相关表述,即“具有一定的市场知名度、为相关公众所知悉的企业名称中的字号,可以认定为企业名称”。
“有一定影响”“知名”的判断标准是否应当统一存有一定争议。部分观点认为,将“有一定影响”解释为“知名”,实际是降低了司法保护标准,通常理解下,“知名”的判断标准要高于“有一定影响”,“有一定影响”“知名”和“驰名”是一个逐渐递升的证明标准。而孔祥俊则认为知名商品之类的表述容易被人滥用为追求荣誉称号,故新修订的反不正当竞争法借用了商标法“有一定影响”的表达。在解释上,“有一定影响”与“知名”的标准应当是一致的。[6]
笔者认为,“有一定影响”与“知名”的司法认定标准应当是一致的,只是措辞不同而已。《民法典》第107条规定“具有一定社会知名度”的表述同样与“有一定影响”“知名”的判断标准应当是一致的。
具体而言,字号知名的证明标准可以参考反不正当竞争法司法解释关于“知名商标”的认定标准,结合字号持续使用的时间、相关公众将字号与特定经营者建立起稳定的联系、企业的规模、盈利状况、进行广告宣传的持续时间、程度和范围、企业名称或字号受到仿冒的具体情况等因素,进行综合判断。
(二)被诉侵权人存在故意擅自使用他人字号的行为
《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六条第一款第(二)项将侵害字号的行为表述为“擅自使用”,《企业名称争议处理暂行办法》(2021年2月24日征求意见稿)第二条、第十九条规定,企业名称争议指企业认为他人自主申报行为违反诚实守信原则,已登记注册的企业名称与本企业名称近似,侵害本企业名称合法权益的情形。目前法律及相关司法解释并未明确界定“擅自使用”的内涵。司法裁判实务中,司法机关通常将不当使用字号的行为认定为擅自使用。而不当使用行为主要包含两个方面,即被诉侵权人商业性地使用了字号,且存在主观恶意。
商业性使用的认定主要依据反不正当竞争法司法解释第七条的规定,即被诉侵权人将字号或企业名称用于商品、商品包装以及商品交易文书上,或者用于广告宣传、展览以及其他商业活动中。
主观恶意的认定则主要考察被诉侵权人是否对具有竞争关系的在先字号予以合理的避让,是否知晓或应当知晓权利人的经营发展状况,是否拥有合理使用涉案字号的依据,及主观上是否具有“搭便车”及攀附他人商誉的意图。
(三)被诉侵权行为足以造成相关公众的混淆
《民法典》和《反不正当竞争法》及其司法解释所称的造成混淆,既包括对商品来源的混淆,也包括对市场主体关联关系的混淆。前者是指消费者对商品上使用的商标判断是否属于同一来源产生误认,后者则是指消费者对相似商标所属主体是否具有关联性产生误认。需要说明的是,混淆行为的认定并不要求以实际造成混淆后果为构成要件,而是要求足以使相关公众产生误认,即具有较高的混淆误认盖然性。
实务中,各地法院的裁判尺度尚不统一。如上海高院审理的(2019)沪民再5号上海益朗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侵害商标权纠纷审判监督民事判决书中认为,是否构成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六条中的擅自使用,关键在于是否造成公众混淆,即将擅自使用与混淆的认定融合在一起,以混淆的认定来证明被诉侵权行为构成擅自使用。但是最高院在30号指导案例:(2012)津高民三终字第0046号兰建军、杭州小拇指汽车维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诉天津市小拇指汽车维修服务有限公司等侵害商标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案中,倾向于将擅自使用与混淆作为两个不同的构成要件进行单独认定。
笔者认为,在权利人举证证明字号具有一定知名度,而被诉侵权人存在不当使用行为时,混淆的证明责任实际已经基本完成。权利人的在先字号具有一定知名度,作为有竞争关系的被诉侵权人在进行企业登记和使用字号时就理应予以合理避让,否则其具有较高的攀附在先字号商誉的可能性。此时被诉侵权人“搭便车”的行为容易引起相关公众的混淆误认,且其希望引起相关公众混淆以谋取更大的利益。所以混淆盖然性的高低,与字号的知名度及被诉侵权人的擅自使用行为密切关联,甚至在特定情况下可以与擅自使用的证明互为表里。

如前所述,字号作为企业名称核心组成部分,其功能与企业名称高度重合,在此情形下没有必要在企业名称权之外单独设立字号权。因此非知名字号是否可以获得保护及如何保护,在理论和实务界均有争议。
主流观点认为,非知名字号不应当作为企业名称进行保护。原因在于《民法典》和《反不正当竞争法》及其司法解释等法律法规均明确规定,具有一定知名度的字号才可以作为企业名称权扩展保护的内容。在字号权没有必要单独设定的情形下,对企业字号的保护应当限定为知名字号,法院裁判不应当超越立法而在审判活动中创制法律。
部分观点认为,可以通过扩张解释的方式保护非知名字号。在北京易用软件有限公司与北京易用软通科技有限公司不正当竞争纠纷一案中,法院认为,尽管原告未能证明其字号“易用”的知名度情况,但是企业名称最能起到区分作用的核心部分是公司的字号“易用”,鉴于原告与被告的工商登记住所地均为北京市海淀区,同为经营应用管理软件的公司,属于在同一区域内具有竞争关系的企业,被告在自身拥有登记注册的企业名称的情况下,仍在经营、宣传过程中大量使用“易用软件”等字样,足以造成相关公众对两个企业及其产品来源产生混淆和误解,甚至可能导致相关公众误以为易用公司是在冒用其他公司的名义或产品,构成对原告企业名称的违法使用,进而认定被告行为构成擅自使用他人企业名称的不正当竞争行为。
第三种观点认为,可以适用反不正当竞争法的原则性条款保护代表企业法益的非知名字号。当经营者的字号使用行为足以造成市场混淆时,如果仅因在先字号不具备法律规定的知名度而不予保护,既扰乱市场秩序,又损害其他经营者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与反不正当竞争法的立法宗旨和目的相背离。因此,应当根据维护公平竞争和制止市场混淆的需要,对不具备知名度的字号予以保护。如果当事人的字号客观上被他人使用并导致混淆,且在后使用者主观上存在不正当的意图,则即使该字号达不到知名的条件,当事人仍可依据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条的原则性规定而受到保护。[7]
笔者认为,不应当通过扩张解释的方法将非知名字号纳入企业名称权的保护范围,对字号的企业名称权保护应当限定为知名字号。
但是非知名字号虽不能获得企业名称权的扩展保护,其作为一种法益依然可以在满足一定要件的情形下受到反不正当竞争法原则性条款的保护。在2021年8月27日公布的《山东法院知识产权典型案例选(2001-2021)》中,山东高院在威尔德摩德公司诉济南慧邦汉默实业有限公司等不正当竞争纠纷案中认为,尽管外方权利人未举证其企业字号具有知名度,但确有证据证明被诉侵权人恶意进行攀附的情况下,被诉侵权人使用外方权利人字号的行为违反了反不正当竞争法所倡导的诚实信用原则和公认的商业道德,扰乱了正常的社会经济秩序,构成不正当竞争,故适用反不正当竞争法的原则性条款支持了外方权利人的诉求。
因此非知名字号虽不能获得企业名称权的保护,但是可以适用反不正当竞争法原则性条款对非知名字号进行保护,只是此时法律所要保护的并非企业名称权而是一种公平竞争的法益。所以非知名字号获得保护的司法判断标准,应从反不正当竞争法“鼓励和保护公平竞争,制止不正当竞争行为”的立法目的出发,结合诚信原则及商业道德,原被告的竞争关系程度,字号的显著性,被告行为的正当性和主观状态,混淆的可能性等多方面因素进行综合考察。
【参考文献】
2.王蔚,关于企业字号权的及其保护的法律思考,法制博览,2017年第18期。
3.任先行、周林彬:《比较法导论》,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47页。
4.张安民,《商法总则制度研究》,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405页。
5.陈乃蔚、魏来,字号权的知识产权特征及其相关权利冲突研究,科技与法律,2001年第1期。
6.柯尚华,我国字号权法律保护问题研究,同济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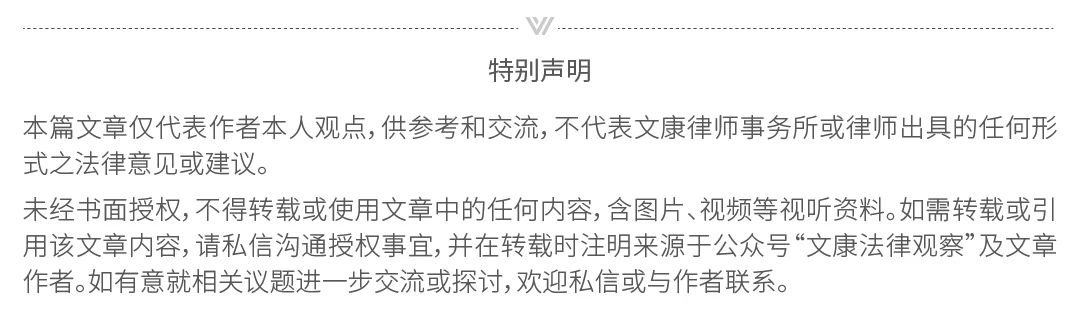
本文作者
专栏文章
-
知识产权
企业出海中的常见知识产权风险及应对措施
本文结合最新行业数据与典型案例,拆解出海浪潮下的知识产权风险与破局之道。2025-11-27 -
知识产权
网络信息作为现有技术抗辩证据的认定
专业解读2025-07-21 -
知识产权
商标侵权惩罚性赔偿裁判逻辑探析
本文通过两起典型案件,结合相关司法解释,剖析商标侵权案件中惩罚性赔偿的裁判逻辑。2025-06-20 -
知识产权
保税仓库知识产权风险防范探析
全国知识产权宣传周2025-04-22 -
知识产权
知识产权诉讼中共同侵权的构成要件及责任承担
全国知识产权宣传周2025-04-21 -
知识产权
数据资产保护路径与登记功能——以北知院首例已登记数据资产不正当竞争纠纷案为例
本文在梳理本案判决的基础上,结合相关理论研究,探讨数据资产的保护路径以及数据知识产权的登记功能。2024-08-27 -
知识产权
驰名商标在民事侵权诉讼中的认定路径探析
专业解读2024-04-26 -
知识产权
字号保护的司法判断标准
本文通过梳理相关资料,详细阐释字号获得保护的法律构成要件和司法裁判标准。2024-04-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