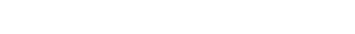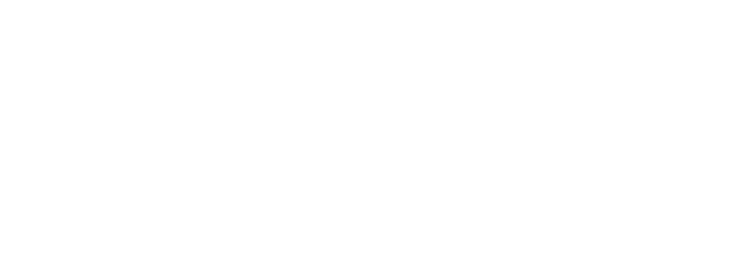本文拟结合现有的地方司法文件及最高院相关司法案例,针对“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的内涵、三种既有情形的理解和兜底条款的实践争议进行探讨,以兹对公司解散纠纷中“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的认定问题有所裨益。

总体来看,对于“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的内涵,实践中存在经营管理并存说与管理困难说两种观点。
经营管理并存说认为“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包括公司外部的经营困难和公司内部的管理困难。其中,经营困难是指公司的生产经营状况发生严重亏损的情形,而管理困难则是指公司的股东会、董事会等公司机关处于僵持状态,有关经营决策无法作出,公司日常运作陷入停顿与瘫痪状态。对此,山东省高院[1]、上海市一中院[2]、最高院(2021)最高法民申6453号、(2019)最高法民申1474号、(2011)民四终字第29号民事裁定书[3]等均持该观点。
管理困难说则认为,“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专指公司内部管理决策层面出现困难,不能简单就字面意思理解为“经营困难”与“管理困难”并存。基于这一观点,在公司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等内部机构已经陷入僵局的情况下,即使公司经营并未处于亏损状态,也不能成为公司解散的阻却条件。最高院在(2017)最高法民申4437号、(2017)最高法民申2148号民事裁定书[4]中均采用了这一观点。
对此,笔者认为公司经营状况往往是其管理状况的外部体现和延续,因此仍应当尊重《公司法》的立法本意,只有当公司内部管理陷入僵局且公司经营持续亏损并无法扭亏为盈的情况下,才能认定“公司经营管理存在严重困难”。
但是,在认定的过程中,一方面,应当将“管理困难”的认定放在首位,不应将二者并行处理。对此,即使是赞同并存说的山东省高院,也曾在《关于审理公司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第13条中提到“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的侧重点在于公司管理方面存有严重内部障碍,如股东会机制失灵、无法就公司的经营管理进行决策等,不应片面理解为公司资金缺乏、严重亏损等经营性困难”。另一方面,应当对何为“经营困难”作出限定,对此,可以参考上海市一中院在《公司解散纠纷案件的审理思路和裁判要点》中的观点,即“公司经营性的严重困难并非短期的经营不善或严重亏损,通常需要考虑公司是否长期处于亏损状态、是否具备扭亏为盈的能力、是否造成股东经济利益的重大损失等情况”。

(一)公司持续两年以上无法召开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
对于《公司法解释二》第1条规定的第一种情形,一方面,最高院及各地法院强调“两年以上”的时间须为持续的状态,不能将股东暂时的矛盾认定为公司僵局。另一方面,针对股东以“公司客观上持续两年未召开股东会”为由提起公司解散之诉的,最高院在(2020)最高法民申2318号、(2019)最高法民申5183号、(2019)最高法民申2477号民事裁定书[5]中均认为,公司在客观上超过两年未召开股东会并不等于无法召开股东会,更不等于股东会议机制失灵,不能单纯以是否超过两年未召开股东会作为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的判断标准。
换言之,《公司法解释二》第1条该项情形所强调的是连续两年以上“无法”召开股东会或股东大会,仅限于“应当召开而不能召开”的持续状态。对于客观上能够召开股东会或股东大会却不召开,并反而以此为由申请解散公司的,法院通常不予支持。
(二)股东表决时无法达到法定或者公司章程规定的比例,持续两年以上不能做出有效的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
基于商事实践的复杂性、公司管理机构决策规则的多样性、持股比例设置的不确定性等多种因素,在实践中,当股东之间或董事之间发生矛盾,造成“不能做出有效的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的原因通常是多方面的。从笔者检索到的案例情况来看,除因无法召开股东会或股东大会外,无法作出有效决议的常见典型情形通常包括:
第一,公司章程所设置的决策比例较为严苛,如约定全部决策事项均须全体一致决等。如最高院在(2018)最高法民申280号海南龙润恒业旅业开发有限公司、海南博烨投资有限公司公司解散纠纷案中认定“根据龙润公司《公司章程》关于“股东会会议应对所议事项作出决议,决议应由全体股东表决通过”的规定,龙润公司已难以形成有效的股东会决议,股东会机制已经失灵,龙润公司陷入僵局”。
第二,特殊表决事项无法得到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股东通过。如最高院在(2017)最高法民申4437号何广林、清远市泰兴房地产有限公司公司解散纠纷案中,以“根据各股东的持股比例,针对要求三分之二以上有表决权股东通过的重大事项表决难以形成有效决议”为由,认定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
第三,持股比例各半的两派股东意见相左,难以形成有效决议。如江苏省高院在(2010)苏商终字第0043号林方清诉常熟市凯莱实业有限公司、戴小明公司解散纠纷案中认为“凯莱公司仅有戴小明与林方清两名股东,两人各占50%的股份,凯莱公司章程规定股东会的决议须经代表二分之一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且各方当事人一致认可该二分之一以上不包括本数。因此,只要两名股东的意见存有分歧、互不配合,就无法形成有效表决,显然影响公司的运营”。这一案例后续被最高院列入第8号指导案例,最高院在(2017)最高法民申4394号广西南宁红白蓝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刘礼宁公司解散纠纷案中也对这一裁判规则予以适用。
(三)公司董事长期冲突,且无法通过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解决
商事实践中,公司董事通常由股东各自委派,董事之间的长期冲突实际上是股东矛盾对立局面的重要体现,本项所规定的是“董事会僵局”被作为“公司僵局”的一种,其实质是公司股东矛盾对立的外化形式。因此,在司法实践中,对于股东之间存在大量诉讼、仲裁等矛盾对立的局面,法院通常也将其作为该种情形的表现形式之一予以采纳和佐证,如最高院(2019)最高法民申6231号、(2018)最高法民申3498号民事裁定书[6]等。

除上述情形外,《公司法解释二》第1条还设置了第四项兜底条款,即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的其他情形。对于这一兜底条款的理解,应当从“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的核心内容出发。对此,司法实践已经基本达成共识,即“判断公司的经营管理是否出现严重困难,应当从公司股东会、董事会或执行董事及监事会或监事等组织机构的运行状态进行综合分析,其侧重点在于公司经营管理是否存在严重的内部障碍”,具体可参见最高院(2019)最高法民申2477号、(2018)最高法民申280号、(2017)最高法民申2148号、(2017)最高法民再373号民事裁定书以及指导案例8号江苏省高院(2010)苏商终字第0043号民事判决书[7]等。
由于上述判断标准仍较为笼统,司法实践中对于哪些具体情形能够被纳入兜底范围,仍存在争议。由于个案情况不同,争议情形较多,笔者无法一一列举,仅选取实践中争议较大的两种情形进行剖析。
(一)“大股东压迫”情形能否构成“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
所谓“大股东压迫”,是指因大股东决策比例优势导致部分投资者作为股东的权利和意志无法通过决议形式得到合理考虑的状况。山东省高院曾在(2016)鲁民终1202号浙江林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济南三川生态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公司解散纠纷案中将“大股东压迫”作为《公司法解释二》第一条所规定兜底条款的情形之一,陕西省高院民二庭也曾在《关于公司纠纷、企业改制、不良资产处置及刑民交叉等民商事疑难问题的处理意见》第4条[8]中将“公司董事、实际控制人压迫的确存在”作为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的佐证。但从司法实践的整体情况来看,“大股东压迫”是否构成“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的情形之一,仍存在较大争议。
一种观点认为构成“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如最高院在(2017)最高法民申4437号、(2017)最高法民申2148号民事裁定书[9]中均曾将股东、董事决策比例较高导致权力行使失控作为“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的情形之一。另一种观点认为不构成“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如最高院在(2017)最高法民再373号广西大地华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刘海公司解散纠纷案中表明:“公司的法人性质及多数决的权力行使模式决定公司经营管理和发展方向必然不能遵循所有投资人的意志,会议制度的存在为所有参与者提供表达意见的机会,但是最终的结果仍应由多数决作出,除非有例外约定。刘海作为持股比例较低的股东,在会议机制仍能运转的前提下,若认为其意见不被采纳进而损害自己的利益,可采取退出公司等方式维护自己的权益,据此主张公司应当解散的理由不成立”。
对此,笔者认为第二种观点更具有合理性。第一,是否会出现大股东压迫的情况在公司设立之初,股东之间针对股权比例、决策机制进行设计和协商时就已经具有预见性,并非在公司内部机构运行过程中才出现的新状况,是股东之间自由意志的体现,以设立公司的合意作为解散公司的理由是不合理的。第二,若小股东认为因持股比例不占优势导致权益受损,可以通过知情权诉讼、退出公司等方式进行维权,解散公司并非其实现权利的唯一途径,这与《公司法解释二》第1条第2款[10]规定的精神也不谋而合。
(二)董事会或个别股东、董事发挥实际管理职能时能否类比股东会相关情形
股东会作为公司在一般情况下的最高权力机构,公司僵局的认定通常是针对股东会能否正常运行而进行的。但个案中,实际发挥管理职能的可能并非股东会,还有可能是董事会或者个别股东、董事。在这种情况下,是否能够类比股东会的相关情形进行公司僵局的认定?从司法实践情况来看,总体上存在两种情况:
一种是公司不存在股东会或股东大会,董事会即为公司唯一最高权力机构,如外商投资企业。在这种情况下,最高院在公报案例(2011)民四终字第29号仕丰科技有限公司与富钧新型复合材料(太仓)有限公司、第三人永利集团有限公司解散纠纷案中认为,董事会作为公司最高权力机关,直接行使董事会和股东会的双重职能,并认定董事会长期无法召开也无法形成有效决议的状况构成公司僵局。
另一种是公司存在股东会或股东大会,但公司实际管理、决策权力掌握在个别股东、董事手中,股东会或股东大会不发生实际作用。在这种情况下,最高院在(2021)最高法民申3042号张学成、海南天懋投资有限公司等公司解散纠纷案中认为,虽然公司存在股东会,但其自成立起就不是通过召开股东会进行决策运作的,而是由个别管理者协商决定的,因此即使公司从未正式召开过股东会,也无法通过有效的股东会决议,但不影响公司开展正常的经营管理活动,不足以认定公司管理存在严重的内部障碍。
由此可见,认定公司僵局的关键实际上在于考察公司实际管理、决策机构的运行状态或个人的决策能力,进而判断公司内部是否能够实际运行。在不存在股东会或者主要管理机构不依赖股东会的情况下,即使从未召开过股东会或无法做出有效决议,只要承担主要管理职能的机构或个人能够做出决策,法院通常不会认定公司陷入僵局,这也贯彻了司法实践中对公司解散一直以来的审慎态度。

总体来看,法院对于公司僵局的认定仍保持着相当保守和谨慎的态度,将其作为解决股东矛盾对立的最后途径,只要存在其他途径能够解决争议,法院就几乎不会认定公司僵局。同时,法官对于公司僵局具体情形的认定处理上却比较灵活,核心在于考察内部机构运行的实际情况,并未局限于现有法律法规所列举的三种情况。
笔者认为,在司法实践的审慎对待和灵活处理的整体方向之下,股东在公司解散之诉中的主张和举证亦不必囿于《公司法解释二》第1条列举的三种既有情况,而应当从公司解散的基础出发,针对“股东已经长期矛盾、对立,丧失信任和合作的基础,进而导致内部机构运转失灵”这一公司僵局的核心问题提供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让法官相信公司僵局已经形成,进而争取法官心证,实现诉讼目的。
【注释】
2. 参见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3月28日颁行的《公司解散纠纷案件的审理思路和裁判要点》。
3.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2021)最高法民申6453号公报案例:陈龙与陕西博鑫体育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等公司解散纠纷案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申1474号公报案例:吉林省金融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吉林省金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宏运集团有限公司公司解散纠纷案民事裁定书以及(2011)民四终字第29号公报案例:仕丰科技有限公司与富钧新型复合材料(太仓)有限公司、第三人永利集团有限公司解散纠纷案民事裁定书等。
4.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2017)最高法民申4437号何广林、清远市泰兴房地产有限公司公司解散纠纷案民事裁定书及(2017)最高法民申2148号公报案例:吉林荟冠投资有限公司及第三人东证融成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与长春东北亚物流有限公司、第三人董占琴公司解散纠纷案民事裁定书等。
5.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2020)最高法民申2318号昆仑能源(辽宁)有限公司、昆仑能源(鞍山)有限公司公司解散纠纷案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申5183号栾立华、聊城鲁西纺织有限责任公司公司解散纠纷案民事裁定书以及(2019)最高法民申2477号赵旭峰、陕西义禧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公司解散纠纷案民事裁定书等。
6.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2019)最高法民申6231号山东博斯腾醇业有限公司、昌邑永盛泰供热有限公司公司解散纠纷案民事裁定书、(2018)最高法民申3498号内蒙古瑞安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内蒙古乾盛房地产有限责任公司公司解散纠纷案民事裁定书等。
7.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2019)最高法民申2477号赵旭峰、陕西义禧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公司解散纠纷案民事裁定书、(2018)最高法民申280号海南龙润恒业旅业开发有限公司、海南博烨投资有限公司公司解散纠纷案民事裁定书、(2017)最高法民申2148号吉林荟冠投资有限公司及第三人东证融成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与长春东北亚物流有限公司、第三人董占琴公司解散纠纷案民事裁定书、(2017)最高法民再373号广西大地华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刘海公司解散纠纷案民事判决书以及指导案例8号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2010)苏商终字第0043号林方清诉常熟市凯莱实业有限公司、戴小明公司解散纠纷案民事判决书等。
8.《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二庭关于公司纠纷、企业改制、不良资产处置及刑民交叉等民商事疑难问题的处理意见》第4条规定:第一、准确掌握公司解散的条件。人民法院适用新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三条判决公司强制解散时,应当着重审查以下三个方面:(1)公司僵局或董事、实际控制人压迫的确存在。主要是指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并陷入僵局,股东对打破这种僵局无能为力,公司僵局的继续存续将使股东和公司遭受不可弥补的重大损失;或者公司董事、实际控制人正在或将以非法的、压制的方式行事,使公司财产的管理或处分显著失策,危及公司存立等情形……
9.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2017)最高法民申4437号何广林、清远市泰兴房地产有限公司公司解散纠纷案民事裁定书、(2017)最高法民申2148号吉林荟冠投资有限公司及第三人东证融成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与长春东北亚物流有限公司、第三人董占琴公司解散纠纷案民事裁定书等。


张慧

文康商事诉讼与破产清算团队
文康商事诉讼与破产清算团队自2007年设立以来,先后担任百余家破产、重整与强制清算企业的管理人、清算组、投资人顾问及债权人、债务人顾问,组织和主持了大量的企业破产与清算工作,擅长从各个角度权衡判断商业风险并及时提供代表各自利益最大化的建议和解决方案,专业能力得到各级司法部门和当事人的高度评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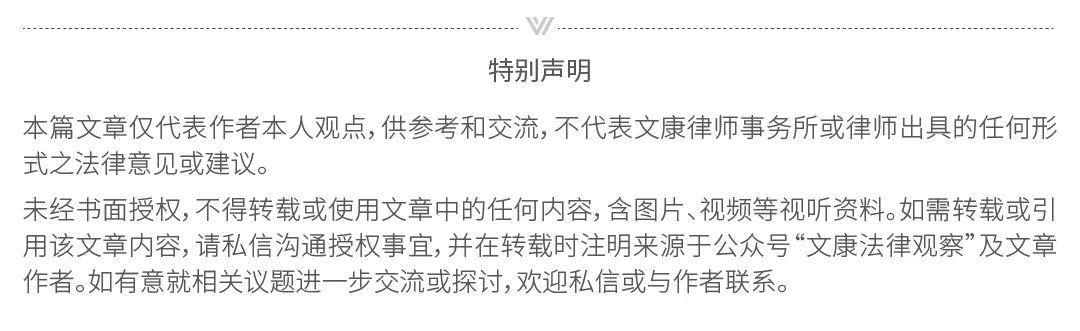
本文作者
专栏文章
-
争议解决
公司解散纠纷中“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的认定
本文拟结合现有的地方司法文件及最高院相关司法案例进行探讨。2024-06-07 -
争议解决
股东如何抗辩怠于履行清算义务的连带清偿责任
笔者以有限责任公司为例,对该款规定在司法实践中股东可主张的抗辩事由展开讨论。2023-10-20 -
争议解决
土地出让金返还条款的效力认定及风险防范
本文由高慧律师结合最新观点,对其中土地出让金返还条款效力认定的具体思路及风险防范展开详细论述。2023-07-18 -
争议解决
交通事故纠纷中“第三者”的身份认定
专业解读2023-06-28 -
争议解决
“高空坠物”事故中提供劳务受害者的救济途径
笔者以近年代理的一件高空物件脱落引起的劳务受害案为例,分析此类案件中提供劳务受害者的救济途径。2023-05-31 -
争议解决
争议解决视角下对赌协议纠纷问题解析
随着中国公司法的修订,新的理念和原则亦或将对赌协议纠纷的裁判和商业实践带来新的变化,与目标公司对赌的实际履行、投资人的权利救济路径等问题,依...2023-05-30 -
争议解决
“职业打假人”消费者身份的认定——以山东省高院某再审案件为例
如何规制“职业打假”行为,在法律适用和解释上仍有值得讨论和阐释的空间和意义。2023-05-29 -
争议解决
从合同纠纷的司法实践难点出发——可得利益计算路径的探究
本文拟从现有规定及法官会议纪要、最高院判例及相关文章中,分析可得利益主张的依据、性质及计算方法。2023-05-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