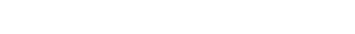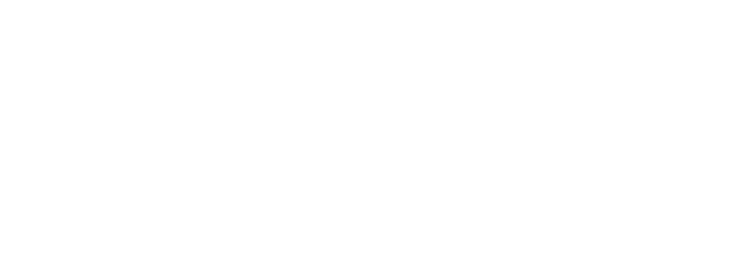摘要:股权代持作为目前一种较为常见的持股方式,在实践中广泛被股东应用,在婚姻家事领域夫妻离婚分割一方持有的股权时,经常存在另一方以所持股权为代持进行抗辩,法院在审理股权代持案件中较为慎重,往往通过多方面证据还原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本文论述了股权代持的由来和现状、在离婚案件中股权代持的认定思路,以及虚假股权代持的特征等,着重对司法实践中认定股权代持的代持协议、出资证明、股东权利的行使等进行了阐释,并结合司法判例进行了论理,以此厘清法院的审理思路。
*本文由文康律师事务所家法承法团队特聘顾问、北京君益诚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李凤凡律师指导,在此特别致谢。
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公司已经成为企业家增长财富的重要方式和载体,而企业家一旦涉及离婚问题,一方主张分割经营公司一方持有的股权就在所难免,近年来天价离婚案层出不穷,如360集团实际控制人周鸿祎离婚时,拟将其直接持有的公司446,585,200股股份(约占公司总股份的6.25%)分割至前妻名下,股份价值约89.67亿元[1]。目前的司法实践中,由于离婚一般只涉及原被告双方,不会有第三人参诉,因此一旦公司涉及案外第三人,包括有其他股东或者一方主张代持股权,由于相关的事实难以在离婚诉讼中查清,法院常见的做法是在离婚诉讼中对股权不处理,而是释明可以另诉处理,因此当事人往往提起离婚后财产纠纷处理是否存在股权代持的事实。


对于上市公司,由于涉及公众利益,法律的态度相对有限公司更为严格,依据今年7月1日生效的新《公司法》第140条规定,上市公司应当依法披露股东、实际控制人的信息,相关信息应当真实、准确、完整。禁止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代持上市公司股票。司法实践层面,在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审理的苗某诉吴某合同纠纷案中,法院审理后认为上市公司股权清晰系证券市场的基本交易规范,关系到以信息披露为基础的证券市场整体秩序和广大投资人的合法权益,上市主体的不实信息披露和相关主体对代持行为的刻意隐瞒,违反证券监管规定,有损证券市场秩序和社会公共利益,故《股权代持协议书》无效。吴某与苗某之间的权利义务均系针对A股份公司64620份股权而设定,苗某80万元虽支付至吴某账户,但已用于认购并转化为A股份公司定向增发股份,吴某系按苗某的要求所为,投资购买股份系苗某真实意思表示。故吴某基于《股权代持协议书》取得的并非80万元款项,而是该款项转化而来的股份,苗某无权要求返还80万元购股款。遂判决,《股权代持协议书》无效,驳回苗某的其他诉请[4]。

股权代持是否成立关键在于代持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代持成立的前提下双方形成代持的合意,即双方对于代持形成一致意见。在离婚案件中,显名股东如果以所持股权系代持为由进行抗辩,此时显名股东一方负有举证代持成立的义务,笔者通过进行法律检索,发现司法实践中法院一般重点审查以下要素,查看代持是否成立:
1.书面代持协议
股权代持的合意一般以合同的形式体现,由于代持协议可以还原当时代持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书面代持协议中一般记载代持的具体要素及各自的权利义务等,是体现双方是否存在代持的主要和关键证据。但是实践中由于代持的原因多种多样,部分是由于疏忽大意,部分则不便于采用书面形式等,因此无法提供书面代持协议,而司法实践中往往不会仅凭不存在书面代持协议而直接否定代持关系,此时还需要通过其它的事实和证据来认定股权是否代持,这也是司法的任务和要求。[6]
在双方签订股权代持协议的情况下,由于代持协议可以基本还原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某种层面上适当减轻了主张代持一方的举证责任,相反在没有书面代持协议的情况下,主张代持的一方往往需要承担更多的举证责任,通过各项证据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才能使法官内心确信股权代持关系的真实存在。此外,需要注意的是,个别案件中存在代持协议后补的情形,此时应当结合其他证据进行认定,必要时启动司法鉴定,以此排除可能存在的虚假证据。
2.出资款项实际支付
显名股东主张自己并非真实股东,在没有代持协议的情况下,股权对应的出资款将是非常重要的证据。如果存在较为直接的出资事实,可以证实显名股东主张的被代持方实际出资,则可以作证其主张代持的事实,但是该种情况下仍然要注意款项的性质,在转账时没有明确备注“投资款”的情况下,不能排除借贷、赠与或其他债权债务的可能性,特别是涉及双方存在其他资金往来的情况下,此时更应当尽到审慎注意义务。
在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刘某某、沈某某股东资格确认纠纷案中,沈某某向人民法院请求确认刘某某持有的某公司出资款系夫妻共同财产并要求依法分割,涉及代持的双方没有提供书面股权代持协议,没有提交召开股东会行使股东权益的证据,公司也没有分过红,因此基于以上事实,法院将审查重点放在谁实际履行公司的出资义务上,法院经审查认为,沈某某已提交初步证据证实某公司的注册资本50万元的资金来源。从款项数额及时间衔接上分析,该公司的注册资本50万元系由沈某某从其银行账户通过现金取款以及电汇方式支出,再交由袁某某以刘某某的名义办理缴纳出资的相关手续的可能性较大。根据优势证据规则,一审法院认定某公司注册资本50万元由袁某某、沈某某夫妻共同财产出资正确,刘某某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最终支持一审法院确认出资款系夫妻共同财产。[7]
3.股东共益权的行使
股东权利分为共益权和自益权,共益权是指是股东基于公司利益,同时也为自己的利益而行使的权利,如出席股东会权、召集股东会权、表决权等。股东最重要权利之一就是参与公司的经营管理,如参加股东会、签署股东会决议、参与公司日常管理等,主张代持的一方由于自己并非真实股东,因此行使股东的权利应由隐名股东即被代持方享有,如果其可以提供上述证据证实,则可以部分说明代持的真实性,但是需要说明的是参与公司经营管理并非当然代表在行使股东权利,公司的其他岗位如董事、高管等,也可以基于自身岗位职责行使部分管理公司的职责,在具体案件中应当予以区分。从另一个角度讲,如果主张代持的一方自身参与了公司股东会、董事会,介入了多项公司的日常经营管理,在其自身与公司没有其他关系时很显然难以自圆其说。
4.股东自益权的行使
股东自益权是股东为实现自己的利益而行使的权利,它包括股息、红利分配请求权、剩余财产分配请求权、股份转换请求权、新股认购权、股份转让权以及请求收买股份权等,自益权是股东有财产权,为股东出资的目的所在。[8]主张代持成立的一方在否认自己是真实股东时,如果有证据显示其实际享受了公司的分红,则其代持的主张较难有说服力。因此公司的分红去向对于查明股权的真正所有人也较为重要,可以与其他证据相互印证,验证代持关系是否存在。
5.合理的代持理由
股权代持实际上掩盖了真实的出资人,债权人等通过外部公示无法得知,对于代持方和被代持方均存在一定的风险,因此一般只有存在充分的代理理由的情况下,双方才有动机通过代持的方式处理,因此,主张代持关系成立的一方需要对代持的原因作出合理解释,在司法实践中以此增加法官的内心确认,如果代持的理由非常牵强,甚至难以自圆其说,则较难得到法官的认可。
常见的股权代持动机包括,隐名股东因为特殊身份如公务员等不适合作为显名股东,比公司实际股东人数较多已经达到上限,存在同业竞争、竞业禁止、关联交易回避等情形,为了试图逃避各种监管等等,无论何种原因,存在代持的主观动机需要主张代持者作出一定的合理解释,在缺乏直接有效证据的情况下,是否存在合理的代持动机是影响法官心证的重要因素,因此对于该项证据仍然要引起重视。
6.公司及其他股东认可
如果显名股东并没有实际参与公司管理,相反隐名股东一直积极行使股东权利,其股东身份得到公司或者其他股东的认可,那么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双方之间存在股权代持关系,该方面的主要证据包括被代持方是否与其他股东签订协议或者与公司客户进行沟通等,包括参加公司各种会议、签署相关文件等,也可以通过其他股东对代持知情的往来函件、短信或微信沟通记录来反应。
7.支付代持的报酬
如果存在股权代持的关系,即双方存在委托行为,代持方和被代持方往往存在支付报酬,因此,如果主张代持成立的一方通过举证定期支付代持报酬,则可以增加法官对代持成立的内心确认。虽然该种证据并非证明股权代持关系成立的关键,但是可以与其他证据形成一套完成的证据链,从而使达到优势证据或者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

实践中,特别是在离婚案件涉及分割公司股权时,持有股权的一方较多的采用代持进行抗辩,以此否认夫妻共同财产的认定,进而避免进行分割,甚至部分股东采用低价或者无偿等方式临时将股权转让,该种情形下如果被认定为代持不成立,则仍然避免不了股权被分割的现实,依据《民法典》第一千零九十二条规定,涉及转移隐匿财产的可以少分或不分。
代持股权是否能够被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法院一般按照“以外观主义为原则,以实质主义为例外”的认定标准,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规则,由主张代持成立的一方证明代持事实,在虚假代持关系中,由于双方不存在代持的意思表示,因此其证据往往较为片面或者存在后补的可能性,法院一般会结合证据链进行认定。在陈某与徐某离婚后财产纠纷案中,在主张代持成立的一方提交的代持协议、股权转让协议均为复印件的情况下,由于真实性难以确认,结合其无法对代持的理由和代持协议签订过程作出合理解释,法院最终否认了代持关系,将案涉股份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并进行了相应分割。[9]

离婚案件中显名股东一方以股权代持进行抗辩屡见不鲜,法院在实际审查中需要结合多重证据探究双方当时的真实意思表示,按照“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对于主张代持成立的一方往往负有更重的举证义务,特别是在代持协议缺少的情况下,法院一般会重点审查出资款项,股东的共益权和自益权行使情况以及是否存在合理的代持理由等,只有在各方证据相互佐证的情况下,才能形成法官的内心确信。对于虚假的股权代持情况,由于双方并没有对股权代持形成合意,其可能的证据形式往往较为单薄或者存在后补、伪造的可能,因此相对方可以否定代持的各项要素,击破虚假陈述方的不实言论,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1] 《三六零创始人周鸿祎离婚,分给前妻股票市值近90亿》,载于《北京日报》,网址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62300392159707398&wfr=spider&for=pc最后访问时间2024年2月26日.
[6] 参见赵旭东. 股权代持纠纷的司法裁判 [J]. 法律适用(司法案例), 2018, (22): 3-5.
[7] 参见(2018)湘01民终5992号民事判决书.
[8] 参见刘惠明,安珏. 共益权与自益权的主体偏离刍论 [J]. 高等财经教育研究, 2014, 17 (02): 91-94. DOI:10.13782/j.cnki.2095-106x.2014.02.006.
【参考文献】



本文作者
专栏文章
-
婚姻家事财富管理
配偶打赏主播的钱款能否返还?
专业解读2024-10-10 -
婚姻家事财富管理
“父债子偿”的实务探究
专业解读2024-05-06 -
婚姻家事财富管理
离婚协议中约定转化夫妻财产协议条款效力问题探析
专业解读2024-04-29 -
保全与执行
夫妻共同财产及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与执行实务
本文旨在廓清执行夫妻共同财产案件中的迷雾,为债权人提供切实可行的诉讼和执行方法。2024-04-17 -
婚姻家事财富管理
公司股权代持在离婚案件中的认定路径
专业解读2024-04-02 -
婚姻家事财富管理
遗嘱是场景和情绪价值
专业解读2024-03-11 -
婚姻家事财富管理
最高法新规施行后,浅析彩礼返还二三事
笔者将结合最高法新规及涉彩礼纠纷典型案例进行详细解读。2024-02-28 -
婚姻家事财富管理
司法大数据视角下同居关系分割遗产问题探析——兼谈民法典第1131条的适用
专业解读2023-08-25